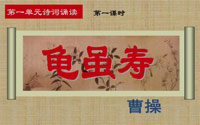課程內容
《海明威的對話藝術》
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其結尾據作者自己說“改了三十九遍,才感到滿意”。海明威苦心經營的就是如何在平靜的語氣中掩蓋內心強烈的大幅度動作。在《永別了,武器》的結尾處,主人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逃亡出來,與愛人會合,到中立國隱居,但妻子卻因難產死了。作者的結尾就是寫男主人公將死在產房的情景:
我走進去陪著卡薩玲,直到她死。她始終昏迷不醒,死時并不拖延。
本來經歷了這么多悲歡離合和人世滄桑的亨利先生應該有多強烈的內心震動啊,但是文風嚴峻的海明威并不讓他的人物像莎士比亞作品中人物那樣長篇大論的宣泄內心苦悶,海明威甚至殘忍地不讓他像契訶夫筆下地馬車夫姚納那樣找尋傾訴地機遇,也不讓他說上幾句連貫性地話。
在房外長廊上,我對醫生說,“今天夜里,有什么事要我做嗎?”
這說明妻子死了,亨利好像很冷靜了,考慮到善后。
“沒什么,沒什么可做地。我送妮回旅館吧!”
“不,謝謝你。我在這里再待一會兒。”
表面上很冷靜的樣子,可事實上并不冷靜。明明沒有什么事,可還是要待在那里。這就留下了極大的空白。在海明威看來,心中所思和口頭表達有錯位,比之心口如一更有利于表現主人公復雜的心理活動。
“我知道沒有什么可以說。我說不出——”
這是醫生感到抱歉,沒有能保全他妻子的生命。但是在這里,他徹頭徹尾無從說起。海明威竭力不讓人物說出自己的心情,他只提供索引,讓讀者自己去想象。
“夜安。”他說,“我不能送你回旅館嗎?”
“夜安”在英語中是晚上告別時的用語,可是說完了告別用語又提出“我不能送你回旅館嗎?”可見醫生并不想告別。
“不,謝謝你。”
“手術是唯一的辦法。”
“我不想談這件事。”我說。
“我很想送你回旅館去。”
“不,謝謝你。”
他走下長廊,我往房間走去。
“你現在不可以進來。”護士中的一個說。
“不,我可以的。”我說。
“目前你不可以進來。”
“你出去,”我說,“那位也出去。”
但是我趕了她們出去,關了門、滅了燈,也沒有什么好處。那簡直是跟石像告別。過了一會兒,我走了出去,離開醫院,冒雨走向旅館。
在這段海明威苦心經營的對話中,最動人之處在于,醫生反復地解釋,說不出口的歉意溢于言表,而亨利卻無動于衷。在這種無動于衷的簡單應對背后又他逐漸強化起來的決心。那就是去跟妻子的遺體呆在一起。醫生的好意和歉意,他都很麻木,而護士的阻攔只能引起他暴怒的把兩個護士都趕走。這一切背景的交代都被省略在空白中,同時又為對話所暗示。大空白和強暗示,正是海明威對話藝術的特點,正是因為這一點,他不動聲色的無背景無外在動作的對話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
在平靜甚至冷漠的應對中包含著逐漸明確、強烈起來的動機,語言所掩蓋著內心變動,同時也就是語言所提示的內心動作,二者錯位幅度越是大,對話的內在分量就越重,就越經得起欣賞。
二十世紀初西方現代小說得對話就是追求這樣內在的不可見的動作,或盡可能省略可見的外在動作的。
拿海明威對話和笛福的《摩爾.弗蘭德斯》中對話一比較,就可以看到在不到三個世紀的歷程中對話作為一種藝術手段已經又了多么驚人的發展。笛福的小說是用第一人稱寫的:
“親愛的,”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們到鄉間去玩玩好不好?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噢,親愛的,”我說,“你要去哪里?”“哪里都可以,”他說,“我很想像貴人王公似的過一星期,我們就去牛津,”他說。“我們怎么去法?”我說,“我不會騎馬,坐馬車又太遠。”“太遠!”他說,“乘六匹馬的馬車到那里都不嫌遠。我要你像個女公爵似的和我出去旅游一番。”“好吧。”我說,“親愛的,這雖然有點胡鬧,可是只要你喜歡,我就依順你。”……
這樣的對話從現代小說的角度看有如中學生作文。它既沒有外在的動作,又沒有內在的動作。心里所想的和口里所說的完全一致,沒有任何錯位。在現代小說家看來除非特殊的激發,心口沒有任何誤差,是不宜用對話,特別是分行對話來表現的。一般來說,這種心口如一的閑聊,么有任何潛臺詞,光有對話而無潛對話,不推動人物內心的變動,應該用極其簡括的敘述幾筆就交代了過去。
此內容正在抓緊時間編輯中,請耐心等待
陳老師
女,中教中級職稱
優秀教師,指導學生參加競賽,教學經驗豐富,教學成績顯著。